【校讯的故事·忆述】
儿时,我每出家门,至邻庄玩耍,或至三里路外的高作镇上购笔墨,母亲都要叮咛再三,防备被狗咬,小心失足落水。1954年,我在盐城中学读至高二,因病辍学,次年夏,申请退学,以社会青年身份,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,从本科到研究生,读了八年多,毕业后,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,后调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。复旦大学是教我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畅游的伟大母亲,而其校训“博学而笃志,切问而近思”是指路明灯,照亮我前进的道路,更似母亲的叮咛,要终身记取,切实遵行。1964年5月,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《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》,经答辩委员会投票通过。走出复旦大学大门,已逾半个世纪,而母校复旦校训,一直像母亲的叮咛,时时在我耳边回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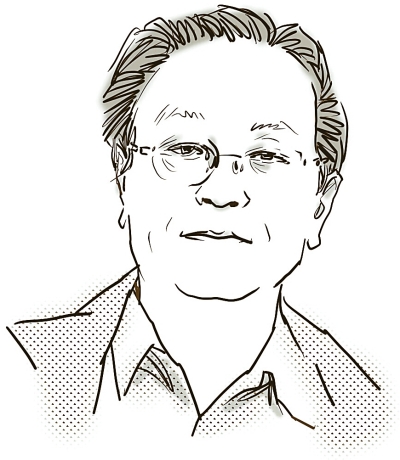
王春瑜素描 郭红松绘
校训源自《论语·子张》:“博学而笃志,切问而近思,仁在其中矣。”事实上,这正是复旦大学优良校风的体现。以我就读的历史系而论,教我们世界古代史的教授周谷城,在课堂上多次告诫我们,要于学无所不窥,由博而约。他本人就是个典范,他不但精通外语,更精通史学,以一人之力,写成《中国通史》《世界通史》,20世纪40年代由开明书店出版。1927年,周谷城投身湖南农民运动,任湖南农会秘书长,打土豪,反封建。大革命失败后,他到上海教书,是著名的反蒋爱国的民主教授。
又如教授周予同,在课堂教导我们,不管见到什么书,都要翻翻,要懂得目录学、版本学,又教导我们,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回忆他与周谷城在五四运动中参与火烧赵家楼,亲眼见到匡互生点火的情景。20世纪40年代,他们是反蒋、反独裁、争民主的“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”主席,有很大的社会影响。
我研究生时的指导老师陈守实,是梁启超的弟子。抗战时,他投笔从戎,参加新四军,任苏南行署文教科长。战争环境下,常要夜行,他眼睛近视很深,骑马甚不便。粟裕同志劝他还是返沪到大学执教为好,他才重回教育岗位。
三位老师以及教授蔡尚思、谭其骧、王造时、程博洪等都是“博学而笃志,切问而近思”的楷模,我荷蒙教诲,幸何如也。
我在复旦大学读本科时,遍读文史书籍,换过三个借书证,读研究生时,在善本书室,有多种康熙初年的刻本,如《砥斋集》《海右陈人集》等,还是我第一个掸去书上的灰尘,以前无人读过。研究生毕业论文通过,等待分配时,又蒙蔡尚思师特别关照,给我一把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室(内部)的钥匙,使我看了包括汉奸、托派、无政府主义者等等的书,开阔了视野,丰富了知识。我关心国事,心忧天下。我是1967年冬上海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“1·28”事件的策划者之一,并写了“点将录”传单。为此,受到张春桥的走狗徐景贤、徐海涛、杨一民、张惠民之流的迫害,我先后三次被隔离审查,直到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,后被平反才停止。在丧失自由的日子里,我“切问而近思”,彻底反思“文化大革命”。从1977年至1979年,我先后发表了《究竟谁是牛金星》《株连九族考》《“万岁”考》《烧书考》等杂文。《“万岁”考》发表后,更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。
20世纪80年代初,我清醒地看到,贪官日多,民甚厌之。为了总结中国历史反贪的经验教训,我主编了近百万字的《中国反贪史》。此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,后由中国出版集团、人民出版社重版,并获得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。事实证明,古今往事千帆去,唯有校训一篷知。我将牢记母校复旦校训,继续前行,生命不止,奋斗不止。
(王春瑜先生原为我院历史学系教授)









